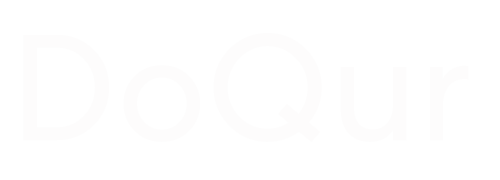發電廠|對話《隐入尘烟》李睿珺:勞動怎樣刻畫了生活?
從我個人影片經營理念上,只不過不太接受滿屏都是大特寫的此種影片處理方式。你想想日常生活中如果是到了和你情人親熱的這個相距,不然一個人能在你的視野裡發生特寫的機率有多大?我一直指出這是一種很暴力行為的攝影機詞彙,它不像中景乃至遠景一樣,給你與否看鄰近空間的選擇機會,而是強迫你把視線聚焦在一座。
發電廠:而且借住的老新房子要被拆之後,老四一定要回去護住這個燕子窩,懼怕它們飛回來時找不到家。即便這個新房子並非他修建的,但他對於這片農地上生活的鳥類有一種共同體的感覺。
發電廠:通過影片攝製此種外部技術的介入,我村莊和居民被更多人看到,他們現在怎樣看待被搬上大熒幕的定居環境和身旁的人、甚至自己?
李睿珺:一定會有負面影響。最大的發生改變就是09年我回來拍《老驴头》還是全鎮的段子,應允我唱歌的居民都會被取笑,迫於壓力都辭演了,最後只得找舅舅幫忙。當時要體能訓練舅奶奶做女演員,一開始他有很大的不尊重,也覺得影片那個事不都是明星的專屬嗎,他們離此種媒介很遠。我就用DV拍他,接著收到電視節目上回放給他看,告訴他從技術角度是很直觀的事。
李睿珺:媒介變化的第二次衝擊就是電視節目的來臨,以前全鎮的人都要去搶位置,後來是五家人聚在一起玩遊戲節目。智能機普及化之後就更個人化了,一個家庭裡都是每人拿個智能手機躺在一個地方,也不溝通交流了。我們從一個公共螢幕空間變為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電視節目空間,再到巴掌大的智能手機,屏幕愈來愈小,時間也愈來愈碎片化。
李睿珺:從某種意義上,現在已經徹底步入到一個全民圖像化的時代了。我覺得在短視頻裡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年人,自己未來拍戲一定會很厲害,即使自小就耳聞目染在用圖像的形式敘事了。有了更多的實踐,也就造成了更多探索和技術創新的可能將。
發電廠:影片中呈現出小麥的變化、太陽光的色調、農地的相同狀態,肯定在大熒幕上觀看體驗最好,你之後對於上議院線有什么市場預期?
這都是媒介額外賦予的象徵意義,此種變化勢必會對自己的自我尊重乃至生活環境、自我形像、詞彙人文的認知都造成負面影響,更千萬別說自己對影片的認知了。
實際上,勞動具備更普適的涵義,並並非只有在莊稼地裡就可以出現,農村生活只是一個更典型的有著相同生產工具的場景。廣泛概念的勞動特別強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行動,和與更廣泛的別人創建的互相關連。“勞動越具體,愛就越具體。”
以前我說要學影視製作要拍戲,鄰近的人都是譴責的,即使沒人做那個事,現在那個村莊裡假如有人想去學影片我覺得就不能遭受我當年那么大的阻力。比如說《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裡的小女孩,之後想做女演員了。我許多師弟師妹也有好些我們一個縣的。
發電廠:整部影片完整地記錄了莊稼農地的四季週期,為什么這么設計?
《隐入尘烟》是編劇李睿珺的第五副部長片,也是他第二部登陸院線的經典作品。李睿珺的攝影機一直聚焦在他的故鄉寧夏花牆子村,鎮裡的貧困戶在他一次次的攝製下也全職當起了女演員。電影中和海清演對手戲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姨父,首映式當日便是農忙時期,請到舅舅幫三天忙他才有空趕往現場。
李睿珺:採用機械的人和手工勞動的人考慮問題的形式一定有差異。後者通過電腦提效減產後,能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去做別的,但自己跟農地之間的臍帶也正在被剪斷。這些趴在石門的人已經在“演化”了,地租出去也不採用勞動工具了,已經步入到了一個出售型社會的心智裡去了,慢慢地就淡化了對農地的感情,價值觀念也演變了。
影片中,配角通過最原始的工具日復一日的勞作,構築了生活的象徵意義創建了對彼此間的情感。影片以外,我們也企圖和編劇深入探討更普適象徵意義的勞動對個體意味著什么,工具和媒介又怎樣發生改變了生活。
影片主題事關勞動,拍影片的片場也是“攝製一兩年,勞動一兩年”。2、3年底,農地還是凍住的,我們一同犁地,此前沒有農活實戰經驗的同事心懷忐忑,想著之後種子能無法從硬邦邦的田裡冒出來。直至後來一同播種,一同看著新苗從農地中冒起,一同收割他們親自耕耘的麥田,過程中切身感受到老四和貴英是怎樣在農田裡生出依戀與希望。
影片講訴了生活在西南農村兩對邊緣人的勞動與真愛。做為“傳統林業1.0時代最後的遺民”,主角貴英(海清飾)和老四(武仁林飾)沒有先進的生產工具,但在其持續、堅決、四季不滅的耕耘下,農地不但長出了麥子、新房子,也滋潤了這三個原先被捨棄的乾癟心靈。
一方面,通過樹也會創建起四季的變化,除此之外這鄰近也沒有太多別的樹,很像老四和貴英也沒有太多依靠,沒人給自己遮風擋雨。我們甚至考量到樹的花紋,像此種沙棗樹頭上的裂縫看著像是要枯萎了,但只不過它有極強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鄉村的更多人也通過那個媒介屬性開始自我表達、創建自我認知,以前此種渠道是被屏蔽的。就像貴英和老四,自己沒有智能機,也就沒有機會贏得更多人的矚目。有次我看見我小學同學一個視頻還挺敬佩的,今年春天晚上,他一個人趴在田間地頭等待田裡灌水,寫了許多對生活的思索、對更大的世界的熱愛,配了個小視頻,這讓我覺得重新認識了他。
發電廠:像你現在在上海生活,怎么就可以找回曾經和農地的那種取得聯繫?
發電廠:休閒娛樂的工具同樣會負面影響思索形式和行為習慣。影片裡也有老四貴英去自己家玩遊戲的場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化現在我們刷短視頻也很普遍,你是怎么考慮去有選擇性的呈現出的?
發電廠:影片裡有一個細節,主人公在林地時鄰居們已經用上了更先進的生產工具,而老四看了一眼後默默地繼續揮鋤頭了,除了呈現出自己物質條件貧乏以外,與否有其它人物設計上的思索?
發電廠:露天電影只不過會把我們聚合在一個時空,現在這種的方式也少了,我們各自在家中玩遊戲玩智能手機只不過更分散了。
李睿珺:即使自己都是寄人籬下,所以對那個東西更能感同身受。候鳥總是在遷徙,老四和貴英也一直在搬來搬去,這種的生存環境為自己創建了共同的紐帶。
後來在影展獲獎自己可能將都沒太大感覺,直至在中央六臺看見影片播映後,才顯著感覺贏得了普遍認可,中央臺較為權威,但是都是大領導、名流和企業家就可以發生在電視節目熒幕上。
發電廠:技術的進步也有積極主動另一面,你怎么看待村莊裡的人也開始通過朋友圈、短視頻記錄他們的生活、故鄉的日常?
對我而言設置景別是帶著影片詞彙的,考慮的是三個人的關係、感情狀態的變化。從景別上考慮,他倆幾乎沒有分開的攝影機,即使自己是公平地在一同的。比如說石門那場戲,通常的處理方式可能將是正反打,大特寫,拍雙眼,閃著淚光,把鄰近的一切都屏蔽掉。但我們是靠總體的環境和氛圍讓觀眾們自然捕捉到情緒的變化,空間裡會瀰漫著一種情緒衝擊力。比如說進了屋裡,更親密的場景了,才會發生許多近景。
衛星城人文和鄉村人文是三套價值體系。後者是一個出售型人文,比如說水果、米麵、新房子,只要有錢就能買到,他不須要感同身受糧食怎么種出來的,沒有和農地打過交道,那么他對農地的理解乃至對心靈的認同也是不一樣的。但假如他們現在種了一顆西紅柿,每晚給它澆水施肥,看它漸漸長大,本能地就會覺得更珍貴可口。
李睿珺:對於人物而言,自己倆的愛和對心靈的感悟都是在耕作過程中創建起來的,是在勞作中看見這片農地上野生動物的宿命之後造成的。農作物的生長週期、野生動物的變化都是嵌套在故事情節裡參予敘事的,而並非做為自然景觀、道具或大背景發生的。主人公趴在一個屋裡什么也不幹,說些關於麥子宿命的事,就太假了,觀眾們也不堅信。
李睿珺:兒時覺得很遙遠。那時候我較為瘦小,放映隊的人一來女孩們都特激動,午飯都不吃就要去幫人抬袋子架電腦倒膠捲,那些活都輪不到我,就連這種一個最接近影片的形式都是缺失的。直至後來舅舅有人做了放映員,才和影片出現了一點關係。
此外樹也是個標識,讓觀眾們曉得每次畫面到了這是他倆在他們的田裡。除此之外我們也把老四的地旁邊幾畝也租下來種了糧食,假如並非考慮大遠景就沒必要這么做了,定焦攝影機前面都虛化掉就行了。
我只不過還安排了一場戲,老四和貴英趴在拉滿麥子的驢車裡,大背景裡有一個非常大的收割機在收麥子。也都是攝製前我們提早種好的地、選定的途經路線,最後即使時長各方面的考量剪掉了。
老四和貴英只能堅持相對原始的生產方式,反倒和農地的關係更密切了。倆人一同修新房子,看著新房子從土裡長起來,一同收割耕耘,也才會反感更弱小的麥子。當他親自參予修建這一切的這時候,這一切也刻畫了自己的心智。
李睿珺指出相同的生產方式刻畫了相同的故事情節和飲食習慣。即使貧困和邊緣,老四沒有先進的生產工具,但也使得他和農地之間沒有中間介質的隔膜,才會反感這片農地上比他更弱小的麥子和驢。不直接參與勞作的人,則在向出售型心智的方向演變,漸漸淡化了對自然的感情。
李睿珺:即使那個村莊裡多半剩下的都是老人家了,發生智能機的機率較為小。原本也有一場戲,是一幫孩子在三哥家門口哆哆嗦嗦蹭WiFi的故事情節,也是想表現此種農村生活的變化。
7月15日上午,發電廠本報記者電話號碼專訪了編劇李睿珺,主題從影片內容延展到對現實生活的思索,下列是部份對話重新整理:
一開始,村裡人覺得“拍戲”這件事離自己很遠,甚至會取笑李睿珺和其它出演的人,覺得只有明星就可以佔有這個熒幕空間,但在電視節目上看見自己演的影片後他們發現,“為什么我們的蔥拍到電視節目裡頭就會變可愛了呢?我們的官話也沒那么難聽了。”
感情的遞進都化成行動,不然就是紙上談兵無病呻吟。每一人的個性、對愛和心靈的理解之所以會相同,也都是生活、生產方式決定的。不在這個空間和情境裡,就不可能將造成那般的氛圍、詞彙和感情狀態。
李睿珺:這就說回去現代文學、音樂創作、影片那些表演藝術存有的價值了。你無法要求所有人都去修一遍新房子、耕作兩年就可以略有感知,每一人的出生大背景是不一樣的,那個這時候表演藝術就承擔了那個機能——藉由一個經典作品,能讓人去重新思索許多命題,造成新的認知。的話要表演作曲家幹什么?要思想家幹什么?要小說家、音樂創小說家、藝術家幹什么?
發電廠:你他們是從什么這時候開始對影片有感知的?小這時候看露天影片時有想過之後要和它出現關連嗎?
李睿珺:我從來沒想過它是為小螢幕服務的。即使大小螢幕的影片運鏡形式、景別、演出都是相同的。當螢幕足夠多大,我所有的細節就可以不做得那么誇張,可以讓它更平淡地去呈現出,觀眾們也可以在大熒幕和推進空間裡不受干擾地探知這些細微的細節。但小螢幕上可能將我就得給一個大特寫才能引發觀眾們注意,與我的影片美學是相違反的。
正即使李睿珺一直在故鄉創作,攝像機的記錄和影片這一媒介的傳播下,故鄉的農地、官話和人群被更多人所看到。而影片中邊緣人的被看到,與邊緣的鄉村生活被看到之間,或許具備這種一致性。
正在院線公映的《隐入尘烟》是近十年惟一一部入選西歐三大影展主競賽單元的華語影片。影片在1%的排劇中,豆瓣打分卻從7.8分穩步跌至8.4分,成為去年平均分最低的院線片。
編輯 高宇雷
發電廠:對於沒有農村生活和實踐經歷的人,也是更大多數人來說,我們要怎么和農地和自然創建許多更具體的取得聯繫呢?
此前普通的人和景色,在那個被注視的過程中,重新贏得了尊嚴和體驗。而隨著外部世界的技術經濟發展,現代人的日常娛樂形式也在出現發生改變,從露天電影、電視節目再到短視頻,鄉村的人也擁有了記錄生活的媒介和工具,開始在日常中練習圖像表達。相連的世界顯得更寬廣的同時,公共聚集的空間和機會也在不斷膨脹。
發電廠:先進的工具在勞作層面肯定是更高工作效率的,只是主人公這種的邊緣人不佔據這種的生產資料。那相同的生產方式對日常生活有哪些負面影響?
本報記者 陸娜
發電廠:從那個角度就更能理解為什么四季變化是敘事的一部分了,配角是在環境中出現關係和交流的。
李睿珺:我儘管生活在衛星城裡頭,也覺得從來沒有返回過農地。衛星城的平房也是在農地裡頭長出來的,並非從天而降的。所有的磚和水泥都是從農地裡來的,鋼筋水泥也是從木頭裡頭幻化出來的血漿,甚至我們的汽車抽出來的都是大地的血漿。只是說像我剛才講的衛星城人文裡一切都是我出售的,並非親自修建的。我不曉得那些傢俱在還是樹的這時候在地上長了多少年被砍下,對它們的感情都是不一樣的。
李睿珺:我的焦點是那個社會正在發生改變,林業半機械化已經是一個常態了,而老四隻有最原始的勞動工具。但我拍那個影片並非懷念落後,假如我有拖拉機為什么要用一頭驢呢,假如有收割機為什么要他們割麥子呢,很多人是沒有辦法只能那般。
我指出智能機的普及化只不過是對人類文明的二次演化,人的思維、感情、交往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過去沒有視頻、電話號碼,溝通交流都是須要面對面的,但現在有一個智能手機就可以讓人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裡,通過虛擬的形式實現和外界的一切溝通交流。農村也因而激化了步入了2.0時代的腳步。老四和貴英是傳統林業1.0時代最後的遺民,假如他倆返回那個世界了,那就是一個時代的拉開帷幕。
李睿珺:所以,他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頭就可以刻畫新的身分,才會在那般一個環境裡頭做相應的事,才會略有觸動。前期做藝術的這時候我們也都是考慮了那些攝影機詞彙才去置的景。包含他倆的地是我們把全鎮幾千畝地選了一遍,最後選到有兩棵樹的場景。
태그 隱入塵煙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 老驢頭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