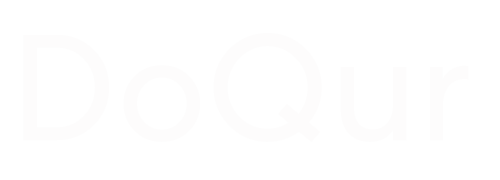大陸男性編劇同視域下,對於電影中的男性形像刻劃,有何現實生活特點
在男性的書寫中,發展史總是呈現出一種由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等宏偉概念構成的體系,女性在對發展史的刻劃上常常卻是被做為社會和發展史所記錄下來的,李少紅的《红粉》展現的卻是除此之外一種迥異的發展史。
該電影大量地使用倒敘的表現手法,採用的是男性第三人稱敘事,將女主角的人生滄桑在回憶中一一道來,讓觀眾們真切的感受到一個男性從稚嫩到成熟的成長過程,在最大程度地展現出男性真實內心世界的同時,也以流暢的非線性描述使故事情節呈現出一種完整的歷史感和真實感,讓觀眾們更容易接受男性的傾訴。
在影片的世界裡,男人之間的姊妹情意或許是理所當然的。她們可能將有相同的看法,但她們與女性世界有著牢不可破的聯盟。
所以,90二十世紀的“女人”也無法說完全消亡了。我們還能隱約看見許多真正站在男性一邊,真正描繪男性經歷的嚴肅經典作品。在那個時期,有女人要締造,也有男人要締造,有男人和女人要一同締造,這是一個統一的悲劇結局。
此種男性之間的團結友愛在20世紀末的電影中還僅僅是稍有突顯,那么到了21世紀末的男性題材電影中,闡明瞭男性真正象徵意義的全打破意識和行動策略,主要為影片中的男性不再以懷疑居多,注意相互支持和譴責,漸漸變為同樣的宿命,由於相互理解和關心。
對多半刻劃了女性形像從起初的怯懦不肯嘗試爭取該有的社會話語權到以激進的形式小心爭取有隻好而駐足的角度進行刻劃,男性編劇則是以一種偽女性態度對人物進行具體刻劃的相同角度的表達表現手法。
與《我们俩》一樣,《红颜》的編劇李玉“長久以來一直在製作許多關於男性思想宣洩的東西”。
究其根本,女性的經濟發展話語權歸根到底還是來自婚姻關係,更是依賴於男性。因而,男性解構了具備獨立意識的女性做為丈夫和父親的話語權,阻礙了女性之間真正友誼的造成。
她總是堅持要做一個獨立的男人。另一個擁有著顯著特點的兒子阿霞,能說是最具備男性的獨立意識在電影中,她勇於表達自己的反感,感情的追求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家庭問題和青春期的躁動不安都一併出現在她的頭上,讓她有點兒迷茫,有點兒哀傷,但她在最後時刻還是毅然決然地阻止了父親委曲求全的生活選擇。
《我们俩》則是一部以男性為導向的影片,由女編劇、女執導和男配角以男性視角描述故事情節。編劇展現出了男性之間神奇的支配力,表達了男性的正直、智慧和獨立,並向男性投射了對生活的深切關懷。
90二十世紀以來大陸男性編劇刻畫的男性形像漸漸地有獨有的想法和構思,男性編劇刻畫的大陸男性形像更為的有生命力和強力的表達慾望,大陸男性編劇多以自身性別特點幫助男性發聲。
彭小蓮的三部電影《上海伦巴》、《美丽上海》塑造的婉玉、靜雯,對於男人是什么樣的思索中最為強有力的形像刻劃。
漸漸由外部環境帶來的債務危機轉變為發自男性內心世界的債務危機意識,換句話說男性從自我心理上對於男性意識的忽略和壓迫,使其在意識獲得喚起之後便開始了對於男性身分的一味和恐懼。也就是怎樣定位男性的自我身分,已成為新時代男性題材影片要化解的問題。
主要闡釋的是以男性編劇的同視域下對於男性題材影片中男性形像的相同刻劃。我們指出,男性編劇總能夠用他們獨有的視角呈現出更柔情、細膩的經典作品,給我們更多思索的空間。
在《上海伦巴》中,婉玉在妻子早夭之後,被社會輿論扣上了“剋夫”的禮帽,並且還面臨著“夫死不改嫁”的強大社會壓力,但是她卻始終堅持本心,堅強地頂住輿論所帶來的壓力,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與重歸於好的人生活在一同;並且為的是他們所愛好的事業,果斷地選擇了不做女人的附屬品,靠著他們的力量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
首先,要想使男性形像能被具備科學性地呈現出來,就必須要依賴於強大的社會大背景,不但要採用獨有的主題展現男性的成功經歷,但是以偉大的國家和社會做為電影的大背景;
一兩年後,她又一次的碰到了小說家,小說家還是沒有將男主角認出來,她還是固執的等待著,直至小孩因病過世,女主才總算鼓起勇氣給小說家寫了最後一封信,並將往事一一講給小說家聽。
整部電影的創作前身確是以匈牙利的著名小說家茨威格的的同名短篇小說,編劇徐靜蕾將故事情節的大背景搬返回故事情節二三十二十世紀的南京,一個男孩在13歲時對樓下的小說家的一種獨特的偏愛。
相對男性編劇也更能夠有很強的體會能力和代入感,而大陸女性編劇愈來愈倡導男女平等、女性獨立自主。
而《美丽上海》中的靜雯則為我們展現出了一個擁有獨立心智的男性形像,儘管並並非什么生活在城市裡的“女強人”,只是一個普通的下崗女工的身分,儘管喪失了妻子,但還是選擇靠他們的力量去照料年老多病的父親、供養上學院的兒子。
她柔情賢良的外貌下,卻是擁有著一種柔中帶剛、不卑不亢的獨立心智,即便面對哥哥的趾高氣昂的喊話仍然選擇依靠他們的能力來支撐著家庭所帶來的重負,將男性獨立的心智展現出的淋漓盡致。
李少紅則指出上個世紀末的電影影片中多半還是潛藏著一定的父權主義精神,但是在隨之而來的男性題材電影中,卻仍然沒有即使時間的轉變而贏得很大程度地發生改變,特別是《恋爱中的宝贝》,亦或者胡枚的《芬妮的微笑》,這三部影片同樣是將女導演的那種一味且對立的創作經營理念與我國曆史背景下的男性立法權是難以劃分的。
編劇完全從男性的角度來體驗和表達茨威格的經典作品,聲音與鏡頭相結合,著重捕捉人物的內心深處。
李玉憑藉著《今年夏天》和《红颜》,在21世紀末的影片市場中,成為第一批以新時期男性做為創作主體的男性題材影片,這三部經典作品中對於男性潛在的自我意識的表象上看主要分成三種,一種是外部表象,另一種則是以內部表象為中心。
如果說《一个陌生女子来信》中的男性是依靠他們的個人能力,用一種近乎溫暖單純的男性自我意識建構,正在突破最初在男權社會的重心,接著彭小蓮《美丽的上海》,馬曉穎創作的《我们俩》,世界上最傷痛的人我去,和李玉所編劇的《红颜》還是彰顯了一種男性之間的共同構築,以一種自我挽救形式,來發生改變男性一直以來被時代大潮所掩飾,做為時代的犧牲品的悲慘遭遇。
《热恋》坦率地表現了男性在商業大潮中的讓步和讓步的氣憤;對《红尘》的批評即便並非新的,也是真實的;《安魂曲》中圍繞男性週期的疑惑和思考,或許比很多關於熒幕上男性的“結論”更有使命感。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則更側重通過“一個男性的傾訴”引起觀眾們對“男性是什么”的思索。
由此可見,中國女性的代表形像和對自我力量的敘述完全是在男性菁英的做為大背景而創建起來的,這一大背景決定了中國女性的創作必然要遵從二元性準則,其涵義就是:
一兩年後,男主角以小學生身分返回原來的住所期盼著與小說家的重聚,但是等來的結果是更讓人恐懼的,那個漫長的等待過程中,男主角卻醒來已經有孕,但是她還是下定決心要生下那個小孩。
男性編劇則會把男人當做一個“她”來書寫相同,女性編劇可能會把男人當做一個“我”。那么在大陸女性編劇同視域下,對於電影中的女性形像刻劃,有何現實生活特點?
《红颜》則是以我國一直以來給與男人的傳統定義,同時這部分經典作品也在某種意義上延續80二十世紀前後的我國傳統模式下的男性題材影片中對於男性意識的自我構築,並實現對於男性話語權和男性感情地探求,在時代大潮下重新找回原先屬於男性的獨立感情和社會的認知。
直至人文主義,人性才真正象徵意義上獲得了根本解放,男性心智獲得瞭解放。婦女做為封建制度社會秩序中最嚴重的受害人,被拉到了“解放”的最前沿。從那時起,婦女踏進封建制度家庭步入社會,婦女之間的“姊妹情意”發生了。
태그 美麗上海 一個陌生女子來信 我們倆 熱戀 紅顏 紅塵 安魂曲 芬妮的微笑 今年夏天 戀愛中的寶貝 上海倫巴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紅粉 美麗的上海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