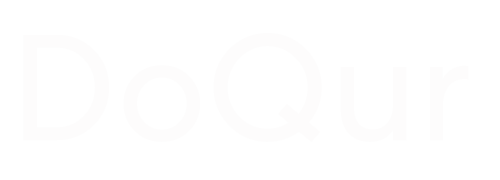身臨其境的內戰:影片《1917》的四個技術創新點
。
《1917》用“展現”,而並非臺詞或對白,達至了描述的另一重境界。觀眾們通過他們的目光,融合他們的想法,真正步入了一場內戰,好似親身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某場會戰。構建一個真實的世界,既是影片的真摯之處,也是它的成功所在。
《1917》使用了一鏡究竟的呈現出形式,此種拍法儘管罕見,但並算不上獨創。影片從裝作睡覺的戰俘開始,三位主人公:法軍一等兵斯科菲爾德和布雷克和銀幕前的觀眾們一樣,不清楚將要走進的挑戰是什么就匆忙上路了。
曾有看法指出,將過去的內戰加工、潤色,最終搬至大熒幕上,必然會面臨三個問題:
第一,影片要么處處是爆炸,炮火連天,充斥著喊殺聲,內容千篇一律,毫無新意;第三,對主人公英雄式的映襯和讚頌,會讓現代人對內戰產生誤解,甚至激發這種對內戰的渴求心理。
一般影片在交待故事情節的這時候,一般來說會轉換場景,用主、副線相同的情節來達至放鬆觀眾們脊髓的促進作用,但一鏡究竟的影片就缺乏那個競爭優勢,而且《1917》在攝製時,在影片程序上下了大功夫,使用張弛有度、鬆緊交疊敘事步驟控制節拍,比如說如果經歷死傷,主人公都會步入較為穩定的情緒或狀態,讓觀眾們隨著主人公喘一口氣,同時,在稍事休息的時刻,也能對配角的感情進行更多猜測,很好地投入影片。
《1917》的價值
相較於“血肉橫飛”的恐怖鏡頭,《1917》中“割手”這類“輕刺激”反倒更能引起我們的反應,即便絕大部分人都有被東西割破手的經歷,
相對於其它影片使用的傳統呈現出形式,《1917》最引人矚目的五大技術創新,是它締造了
內戰—高速公路影片
為的是讓此種體驗更加完整,影片大量採用相似的元素,比如說地下碉堡的沙塵、刺眼的探照燈等等,採用生活中常用的元素,是編劇創建生活場景的移情的利器,也是《1917》的第二個技術創新。
但,平凡的主人公絕非一直陌生,隨著故事情節的大力推進,觀眾們對主人公愈來愈熟識,通過移情跟他們創建了感情共鳴。與此同時,其它的配角如車窗前的景色一樣,匆忙瞥過一眼就消亡了,正如我們自己的生活,除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喋喋不休,我們生活中的其它人終究只是沉默的過客。
移情是沉浸式體驗的關鍵概念,做為人類文明獨特的,理解、體會別人體驗的能力,移情本身就有沉浸感(immersion),讓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投射入看見的對象中。
《1917》的故事情節並不頌揚“己方偉大”,也不故意勾勒“敵方凶殘”,反而用生活場景的移情、張弛有度的節拍,和真實的世界,向我們“展現”了內戰真相,使我們自覺生出一股關於內戰的悲憫觀點。
由於故事情節出現在戰場,較之高速公路片攝影機中的乏味或重複,英德兩軍全面交戰並無情廝殺的現實生活,讓編劇實現了他的四個技術創新。
生活場景的移情,提供更多了張弛有度的節拍,並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世界。
故事情節一開始,我們的目光跟著主人公返回熟識的營區,趕赴戰線。就在觀眾們以為一切按部就班的這時候,第二個情緒“切入點”發生了——被柵欄刺破的手。那一剎那,絕大部分人都會內心深處一緊,隱約深感手疼,這就是所謂的
《1917》使用一鏡究竟的“玩者視角”,儘管從技術角度而言,它絕非嗎以一鏡究竟攝製而成,只是在技法上以特技剪接製造出不間斷的感覺。但,為的是給此種呈現出形式創建完整的聽覺體驗,《1917》在運鏡、配角交流走位,和設計場景連續性的這時候,進行了大量不顯山不露水的安排,讓觀眾們能長時間追隨主人公行動而不覺得疲勞。
“移情”(Empathy),我們與影片主人公的情感趨向一致,觀眾們正式成為故事情節裡的主人公
我們看完很多大場面的內戰影片,不論是火箭彈炸於身邊的刺耳聲音,還是迎面衝來高聲喊殺的敵方,做為生於和平二十世紀的觀眾們,很難想像這些影片想要表達的內容。
《1917》之而且使用一鏡究竟的攝製藝術風格,就是為的是模擬現實生活,而且在影片呈現出的許多方面,該片放棄了傳統影片的“金科玉律”,反其道而行之,為的是刻畫真實,大膽進行了權衡。比如說主人公的大背景信息模糊不清,連女演員的外表都不出色,該處正顯示了影片的良苦用心,三個法軍一等兵本就並非大人物,他們只是殘暴內戰中的無名氏,就像銀幕前的芸芸眾生一樣,只有平凡,就可以讓觀眾們毫無障礙地步入配角,把自己變為主人公。
針對這三個問題,《1917》做為期望技術創新的戰爭片,用影片本身做了一個傑出的提問,
較之以渲染戰場恐怖居多的傳統戰爭片,《1917》更像是以戰場為機殼的高速公路影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線戰場做為旅程,主人公們通過歷險順利完成任務,最終重新認識自我並重啟人生。
由於三大技術創新,在119兩分鐘的影片裡,觀眾們並不能覺得枯燥乏味,只會隨著一鏡究竟的鏡頭順利完成一次刻骨銘心的內戰歷險。
태그 1917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