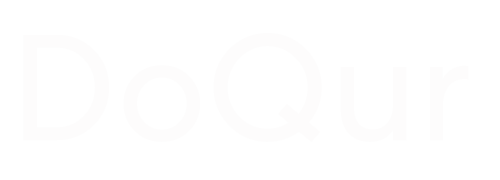當攝影機對準男性的“十級痙攣”,會出現什么?
感覺到新生兒立刻要從下體排洩的一剎那,瑪麗扶著牆衝入洗手間。
換句話說,一名男性在懷孕之後,如果需要自然流產的情形,不然必須要把小孩生下來。
基於此,影片前半段發生了四段“尺度很大”的戲,也就是男主角的四次墮胎經過(前三次失利了)。
首先是讓她懷孕的女友。
相等於白受罪一場,不但沒有成功流產,反倒將陰道黏膜刮傷了。
但是話又說回去,整部影片的存有,僅僅只是為的是給在座的所有男性一個「提醒」,讓我們保護好他們的皮膚嗎?
最後一次,瑪麗不顧醫師的提醒,執意選擇再度進行外科手術。
一旦主動選擇墮胎,就意味著違規了法律條文,實行和輔助墮胎行為的所有人都要一起忍受牢獄之災。
從此,瑪麗在心底作出了一個關鍵的決定:
巧的是,就在昨天我寫這篇文的這時候,好友發來QQ消息告訴我:
圖源:中央電視臺專訪電視節目《半边天》之《我叫刘小样》
讓人居然的是,緊接著,整部片在當年的那不勒斯影展 “主競賽單元”中奪下了 影片獎(金獅獎)。
直至去療養院進行檢查和後——瑪麗接到了兩張《怀孕证明》。
相較於男性,在滿足慾望的過程中,女性不得不忍受更大的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壞結果就是懷孕。
作者:穴鳥
此種這時候,忽然懷孕了......要把小孩生下來嗎?
何況,這種的傷痛並非個例,它可能會出現在每一名擁有陰道的男性頭上。
......
往遠了說,在往後的人生計劃裡,較之「成为母亲」,她更渴求的是對事業的追求,對夢想的追求,和對自我的追求。
面對瑪麗懷孕,女友表現出了事不關己的立場。
彭博社本報記者報導稱,一部名叫《正发生》的比利時墮胎題材電影在放映時因 “墮胎故事情節尺度過大”引發觀眾們心理不適。
“我寧願傷痛,我千萬別麻木,我千萬別我什么都不曉得,接著我就很滿足。”
但別忘了,那個「重新开始」是用一次又一次傷痛換來的。
還記得今年9月第78屆那不勒斯國際影展舉辦前夕,出現了這種一件事:
爽完之後,那個女人用一句 “我能怎么辦,我又並非醫師”快速逃脫,把難題留給瑪麗獨自一人面對。
每天晚上9:30,等你一同用看法撕破世界!
這讓我想到了新聞報導裡不止一次發生的,關於“男孩數次流產”的報導。
男性必須擁有生育是否的基本權利,而並非成為行走的生育電腦;
直至聽到一個東西從皮膚滑出、沉入馬桶的聲音,這才鬆了一口氣。
瑪麗答道:“是的,一種只會反擊男人的病,把她們變為家庭主婦的病。”
它好的地方在於,它太真實了;
《正发生》
那位女醫生告訴她: “那些牆太薄了,不許發出聲響或是呼喊,不然我就會停下來。”
事後,她醒來遲遲沒來月經。
歸根結底,這並非碰到幾個渣男的問題,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壓迫。
事實上,瑪麗後來從除此之外一名醫師那裡獲知,此種名叫“雌二醇”的藥不但沒有墮胎的促進作用,反倒是用以保胎的。
是因為這些年來有曾經受到過壓迫、失去過平等權利的她們,在為我們爭取,為我們付出努力。
為的是能順利墮胎,整個手術過程即便再痛,瑪麗也強忍著一聲不吭。直至最後,大概是痛得真的忍不住了,她又一次仰起頭對著牆壁,發出慘叫聲......
但由於醫師給她的藥並非墮胎藥,而是保胎藥。
再往開了說:
結果引致一名影評人當場昏倒被送至療養院。
與此同時,電影的時間線按照女主的懷孕週數往前大力推進,隨著新生兒在肚子裡的不斷生長,愈發強烈的壓迫感也在向觀眾們襲來。
在瑪麗傾訴了他們想要繼續自學、必須墮胎的“只好”之後,那位男醫生給她開了一種藥,告訴她是用以墮胎的藥。
看著它正出現,不願它繼續出現
但是,接下來,事情的演變卻遠遠遠遠超過了她所預料的那般直觀。
電影中的故事情節大背景出現在20世紀末60二十世紀的比利時——當時,比利時的法律條文上明晰禁止“墮胎”行為。
正如劇中的這段對話,當瑪麗覺得他們可以開始新生活的這時候,她前來找同學,希望能補上之後落下的功課。
須要理解的一點是,有別於當今我們所理解的人工流產。
男性必須擁有公平的接受基礎教育和選擇工作的基本權利,而並非只能在家做家務、帶小孩;
惟一值得慶幸的是—— 抵達療養院後,醫師診斷其為自然流產,換句話說,她無須承擔墮胎的法律責任,總算能開始新的生活了。
圖源:互聯網
整部影片改編自比利時小說家瑪麗·艾諾的一段真實的人生經歷: 年輕時,一次對她導致非常大生理、心理創傷的墮胎。
女主在用他們的“痛”告訴每一名男孩,無論如何,搞好保護措施永遠是第一名。
一句話,道破了整部片的核心—— 它談的不止是男性在皮膚方面的自我保護,更是在談男性的基本權利。
包含這個早先應允幫她墮胎的男醫生,也不例外。
他根本不關心她怎么樣,只在乎他們的市場需求和慾望。
影片《正发生》得獎情形
早上返回家,更是痛得在床邊來回打滾,尖叫聲,捶牆......
雖然編劇為的是增加對男性皮膚的奴役,使用了相對剋制的形式,用大量的臉部特寫去呈現出這三場戲裡的墮胎體會。
手術,從醫師家出來的一剎那,她痛得雙腳無力,一下子沒站穩,下一秒就倒在了馬路上的桌子上。
瑪麗心底很清楚,假如現在選擇生下那個小孩,必然會負面影響她的大好前途和今後的整個人生。
而且——現在,絕對沒用。
而這,也便是今天的我們要關注男性的合法權益,要去為比我們弱勢的男性發聲的其原因。
當瑪麗決定墮胎之後,身為男性的她,漸漸感受到了 「藏匿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男权压迫」和 「女性真正所面临的困境」。
返回臥室時,瑪麗下體依然在流血,最後,電影在她昏迷不醒後被送至療養院的過程中走向開頭。
只可惜,由於體質其原因,外科手術還是失利了。
這位男醫生騙了她,即使在他們眼裡—— “這並非一種男人自己的選擇”,乾脆直接替她作出了選擇。
第二次,按照醫師的囑咐,瑪麗在家給他們口服抗生素,接著偷偷地拿來了父親的襯衫針,消毒後捅入下體,企圖引產。
由此可見,在這部影片裡,男性配角要么處在「缺位」的狀態,要么站在女性的「对立面」。
看完男主角瑪麗的經歷,你的體會是什么?
在這兩點的綜合促進作用下,電影有如海報上的男主角所流露出的鋒芒表情通常,毫不留情扎進所有人的內心深處。
飯後,女人提出想要與瑪麗出現性交的想法,理由是: “你都懷孕了,我們不能有什么的。”
當男性對陰道喪失“自控權”
屢屢求救失利之後,瑪麗決定不再依靠女人,而是他們想辦法墮胎。
我們無法忘掉傷痛——
她在出現性交的這時候抱著僥倖心理沒有采用避孕套,事後開始懼怕,查問我該怎樣補救。
但藉由鏡頭,同為男性的我仍然能夠清晰地感知到那種“男性之痛”。
我覺得是,但也不止是。
眼前,正在上學院的瑪麗處於最好的歲數,便是好好學習的這時候,她愛好文學,討厭寫作,戰績出色;
電影自身所受到的種種褒讚與觀賞者的不適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讓我對整部片子造成了強烈的疑惑。
這種一個 “小片尾曲”的發生,也讓我更為確認了把整部片分享給我們的必要性。
今天,我們沒有即使生下來是男孩而被買下、能夠自由地去唸書、做他們想做的工作,穿他們討厭鞋子......
最近抽空看完之後,總算理解了發生以下那些現像的其原因——
用她如果而言: “有一天我會要個小孩的,但並非以我整個人生為代價,那樣如果我會恨這個小孩一輩子的,我可能將永遠都不能愛他。”
在這種一個前提條件之下,一次派對上,“激素的作祟”讓男主角瑪麗與女同學出現了性交。
但同時,生理上的差別決定了——
女性必須擁有性的基本權利,而並非成為討好男性的工具;
要墮胎。即使冒著生命危險和入獄的信用風險,也無法讓失去對於自我生活的掌控權。
我們過著比影片中的男性們更公平、更有人性的生活。
它更讓人不適的地方在於,它太痛了;
插畫:麻瓜
其二,是一個在幼兒園與瑪麗搭訕的女人。
先天的生理差別決定了男性在這件事情上永遠難以對女性感同身受。
起初,她以為那個看似靠譜的好友可以幫她找出能夠願意給他們墮胎的醫師,居然對方從頭到尾接近她都是帶著 “目的性”的。
和女主瑪麗一樣,時至今日,有許多男孩已經有了 “自我意識”的覺醒。
她們意識到男性也是有慾望的,意識到他們能不再是“被動接受”的一方。
因而,在我看來,所有男性都該去看一看整部影片。
第三次,她又找出了另一名醫師。此次,單是外科手術前的一句“警告”便足以讓人倒吸一口涼氣。
同學問瑪麗:“你之後病了?”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