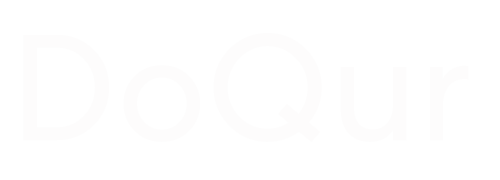感傷沒意思,《东北虎》卻有點兒意思
寓言式的人物,
上一次鶴崗發生在大眾視野,是因為超低的樓價,讓那個地方收留了很多新移民。自己無論從哪個衛星城漂流,最終走進了“樓價的盡頭”——鶴崗。這個和斯堪的納維亞維度接近的衛星城,在凝重茫茫的冬日人煙稀少,西北本土的氣氛又被瀰漫上了兩層斯堪的納維亞式的喧鬧。
觀看經典作品的趣味性就在於,每一個配角和敘事,都在其中看見作者的影子。小二那個配角大概就是這部影片的點題人物,他的存有是耿軍故事情節的魂魄和核心。
但很多這時候,生活的漣漪也像是投置在水底的石子,盪漾起的水紋總會隨之消亡,直到水面恢復如常,就像你的抵抗未曾出現。
直觀地介紹《东北虎》,這是一個多重複仇的故事情節。第一重複仇是男主人印章宇出演的徐東為狗復仇;第二重是家庭感情發生了裂痕,馬麗出演的配角美玲像柯南一樣,去找尋毀壞她家庭平淡的人。一個為狗,是社會性的;一個為情,是家庭性的。聽起來像激烈的故事情節,但被裹在了鶴崗冬日的茫茫雪天。
劇中人物的對白“感傷沒意思”戳中了很多粉絲的調侃脊髓,面對被悄無聲息毀滅的平庸生活,或許最有力量的澄清絕非“躺平”,而是一種混不吝式的荒誕。
《东北虎》影片片花。
同時小二的對白也很精確,樸實真實得令人感動,他言語不清地說“你是忙人”。再無更多三個人之間的交待,但這幾個字精確地表達著三個人之間的取得聯繫。馬千里可能將不記得他了,但是他被一個這么弱小的、貧困的、完全邊緣的,活在角落裡地這么一個人,伸手救下:帶來風箏,帶來錢,帶來食材。
對比起來,徐東是最無力的男主人公。這是一個行動力難以抑揚頓挫的女主角,他被拽進了生活的泥淖,越用力越下沉。這種一個人物,儘管是男主卻像是一個“啞鼓”,鼓芯不響,邊鼓(其它人物)卻震耳欲聾。
耿軍擅於講訴小人物(甚至邊緣人)的故事情節,早年攝製的影片《烧烤》、《青年》、《锤子镰刀都休息》到長片《轻松+愉快》裡各種各樣的小人物悉數登場。有騙子、壞蛋、假禪師、基督教徒、護林員、欠債者……自己並非社會的主流,但在耿軍的電影世界那些人構成了他觀察世界的一整個切面。
他的“寒帶影片”有著什麼樣的特徵?近幾年,“西北巴洛克”的敘事一次次把西北拉返回社會公眾探討當中,但耿軍聚焦的“西北宇宙”又很多不一樣的荒誕美感。
《东北虎》的思索也具備這種的時代功能,大抵我們生活在一個過分喧鬧的世界,信息的碎片每晚充斥在我們的生活裡、頭腦裡、片刻不息。怎樣在聲音之中識別真正的聲音和怎樣在聲音之中聆聽自己的聲音是這一代的青年編劇們無可避免的創作命題。他們在觀察世界的這時候,要成為一個“清醒的人”,時刻警醒著的人,甚至憎惡平庸之惡的人。
在耿軍的影片裡,敘事的節拍總是異常較慢。在整部《东北虎》中,能充份地感受到介乎環境和歌劇之中的真實時間感。我把它稱為“鶴崗節拍”,它的作者性在於並沒有調動觀眾們情緒往下走的意願,故事情節都跟隨著人物內在和根植於歌劇內部的節拍進行敘事。
發表文章 | 走走小姐
你看,他的生活裡並沒有天災人禍,但聽起來你總覺得心在不停往下沉。耿軍常觀察他們故鄉的這些好友,元宵節相約,當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現代人心底的所有防備全都放棄。“每一人的臉上既能看見之後的那個人的影子,又能看見這么十多年他臉上露出來的這些受辱的,或是是這些不如意的,嘆息的那種神態。”
和發小徐剛、張志勇相同,薛寶鶴屬於直接步入到“鶴崗宇宙”的成員,他把耿軍稱為“一個怪異的好友”。“就那個人好奇怪,你曉得嗎?你能理解嗎?就是生活中他可以攢許多錢,比如說幾十五萬去拍戲,但是他們捨不得花20塊錢吃頓飯。”
被“平庸”毀滅是無聲的
耿軍在片場。
劇中年長戀人對這對晚婚妻子說“感傷沒意思”,當它反覆在你的腦海中當中縈繞的這時候,就不但是那個人物的對白,而是劇中所有人一同發聲,自己都說“感傷沒意思”。由一個個體到一個局部、再到整個西北,核裂變式的傳遞和回聲,這種“積極主動地感傷”也好似與整個西北靜靜地順利完成了交流。
那個失利又窮困潦倒的中年男人,即使工程款未果而躲在殘破的新房子裡,整日面對家人的拷問。刻劃馬千里的悽慘十分極致,在此種悽慘裡衍生出來的話劇就成了“荒誕”。但一個切面的悽慘並非生活也並非話劇,在那個故事情節裡還有一個很獨有的配角小二。
但這種一個摳搜的西北編劇,帶著強大的凝聚力共同組成了“鶴崗宇宙”。看完《东北虎》,觀眾們藉著影片,對西北這片農地、鶴崗那個地方的人,有了淺表的瞭解。在空寂之地,回聲都要隔著幾秒鐘就可以傳回去。時間和時間的體感是不一樣的,人在寂寥度日中,太難在生活的慣性裡喪失心底的“不甘”了。
到了夏天,西北是所有人類文明的鄉愁。想在冰天雪地裡停下來,迴歸炕頭享受溫暖。獨有的節拍和熟識的敘事場域,構成了耿軍西北故事情節的基底:風趣又傷感、日常且意境。在異常陡峭的2個半小時裡,每一人都如籠中猛獸,伴隨著察覺到或無知在生活中成為“被路人”。這一兩年“西北巴洛克”的跡象愈發多樣,雙雪濤、班宇、鄭執等西北籍短篇小說家的短篇小說成為了影視製作翻拍市場炙手可熱的現代文學文檔。
鶴崗節拍與“寒帶影片”
耿軍讓一個寓言式的人物運載在了生活裡,也也許是他在生活裡找出了寓言。
徐東那個人物的原型就是他的好友徐剛,一個他熟識的少女夥伴,中年好友。徐東那個人物處於他關鍵的人生階段,他製造了問題,也碰到了問題,他能用他的能力化解那些問題嗎?他一方面照料懷孕的丈夫,而且夜間做完小學老師,夜晚也去開挖掘機;另一方面還有讓他難以放下的男孩小薇;同時,他也要為家庭的除此之外一個成員,就是那隻狗去復仇。
戀人小薇那個配角有點像一個女學生,她和徐東之間的情感,即使禁忌而造成非常大的生機。她莽撞大膽熱烈,而且中年徐東又被吸引又深感無措,在家庭以外三個人的情感甚至沒有“不潔感”。小薇告別的戲,是和徐東小兩口面對面坐著,被隱藏的感情藏無可藏,她梗著胳膊和對方喝了杯告別酒。
只好許多人在耿軍影片的時代就說是在模仿阿基·考瑞斯馬基,也說他是西北戈登·瓊斯。這也是我在耿軍的經典作品裡,深感最美妙的觀影體驗。這些人情往來的底子明明是中國人情社會里衍生的,但在觀感上所有的冷調卻並非常規的本土西北。而劇中的故事情節發生地,是這樣一個遠離北上廣一線、話語中心的邊緣衛星城,樓下是齊齊哈爾,和白俄羅斯相似。人類文明被流放該地,天然攜帶著一種強烈的末世感。而且在電影中,你能看見人在此種時光裡陡峭地、百無聊賴地活著。而且在圖像上有了斯堪的納維亞個性也不足為奇了。
編輯 | 走走 青青子
我們一直指出好的對白是什么?是把對白日常化、生活化、顯得不像對白。但是耿軍是個反著來的編劇,在他的影片裡,所有的日常都能變為散文。
此種不甘既是製作者本身的,也是影片中的配角所呈現出的。馬麗出演的丈夫不甘於喪失他們的家庭,徐東不甘於他們甚至沒有能力保護兩條狗,著名詩人從精神病院出來不甘心小說集仍無人問津,曾經春風得意過的馬千里不甘於如此完結一生。這個到了40歲的西北編劇,始終堅信“人文有力量”,以拍影片的形式在刻畫每一普通人除此之外的人生。
而事實上,對於中國人而言無論你與否去過那兒,都對西北有種很強的親切感——可能將是上世紀90二十世紀以來的電視節目小品奠定了過分夯實的基礎,西北的詞彙和風趣在網絡世界之後就來到了千家萬戶,成為一種DNA記憶存有在我們的兒時中。到了近年來,那些西北小說家的故事情節又提供更多了“新的西北”,在更新著我們熟識又陌生的西北。也有風趣荒謬的根基,但無論是雙雪濤還是班宇,自己的故事情節裡常有六十年代的雋永的感情,不論故事情節技巧多高超,那都並非最重要的。耿軍編劇的影片裡也如此,會讓你在時光裡恍惚,它是現在的故事情節嗎?它是真實的故事情節嗎?
《东北虎》並非一個強故事情節的故事,自然我們等不來一個明朗化的結局。就像平凡的生活,沒有起承轉合,而要繼續前進。
日前,青年編劇耿軍的影片《东北虎》登陸院線上映。兩年半以前,該片就曾在北京國際影片節展映,時至今日才得以上映。一部影片踏上熒幕本身就是場跋涉,編劇耿軍在他的影片表達裡跋涉幾十年,總算等到了整部院線成名作的公映。但對於許多粉絲而言,耿軍編劇並並非一個陌生的名字。
它是夢境和現實生活走到了一同的,自己的西北故事情節。
不得不說,在耿軍的影片發生以前,筆者並沒有強烈地對於影片地理位置的敏感察覺到,也沒有意識到我們對“西北的第一印象”須要更新了。但圖像是直接的,它令我們感受到這些小品式的DNA記憶走到今天,西北更像是笑完之後的“乾咳”。它風趣嗎?依然是有令人捧腹智慧的風趣地域,但貫穿始終的傷感像持續響起的大背景樂。直至整部影片兩遍看完,人似的被“凍麻了”,腦子和嘴脣的反應都慢了半拍。沉浸在荒蕪又層層熱浪的感情中,不知怎樣歸納表達。
看見這兒,會深諳耿軍影片的氣質。即使在那場戲裡,不但發生了一個天使小二,同時也在說明著馬千里那個人物他並非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他並非一個概念上的壞人,或是概念上的失敗者。他可能將在曾經順遂的這時候,也是一個正常人,也能讓人去記著他的好,小二的發生有這種一個敘事的機能在。
粉絲把他和他影片中的人物徐剛、張志勇、薛寶鶴稱作“鶴崗宇宙”。薛寶鶴16年前認識耿軍,他還在當地廣播電臺做本報記者。從上海回來的耿軍和張獻民當時在拍短片,電子設備不夠求救到薛寶鶴那兒。他帶著強烈地疑惑,重新加入了沒有軌道、沒有燈光、沒有搖臂,攝像機是高畫質DV的片場。
與許多院線片一樣,該片公映後也引起了口碑的兩極分化。喜歡的人誇獎它帶勁兒,是西北“考瑞斯馬基”;討厭的人則指出它沉默而破碎,沒有重點。但無論如何,該片的發生讓我們看見了另一種藝術風格鮮明的西北敘事,也看見了一個青年編劇難得的堅持與成長。
編劇耿軍曾經歸納這種省份的影片為“寒帶影片”,它的環境和氣候就是影片裡的一個主人公,這決定著它的敘事形式和故事情節的個性、節拍。第二次觀影《东北虎》對這部影片惜字如金的對白藝術風格第一印象深刻,取得聯繫起鶴崗的氣候,在攝氏三十度的炎熱冬日,現代人為的是留存水分而且儘量少說話,也就形成了西北凝練的詞彙自然景觀,也給了影片觀眾們切膚的“在地感”。
但故事情節講完,你又覺得波濤洶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澎湃的感情從冰縫中炸裂是靜悄悄的,但你分明能感受到那種炸裂和灰燼般的悲壯。這就又是西北了,那個有過白銀時代的地方。
《东北虎》圍繞著主角徐東(章宇飾)的生活和人際關係展開講訴。他的丈夫懷孕了,要把狗放走,他一心想給狗找個好人家,狗卻被馬副經理殺了請人幫忙討債;同時他有一個戀人小薇(郭月飾);以及一個著名詩人好友羅德爾。
“我可能將就是在那個時代裡面語無倫次的人,說不清楚的人。那個時代這么喧鬧,雜音那么多,但我什么也聽不到。只不過我曉得,我的表達在那個時代而言,可能將尤其微弱,但我要表達。”
而耿軍的故事情節漂亮的地方就在於,它綜合的講訴能力讓那些無關的人物造成戲劇化:一個士大夫,去找社會人馬千里復仇。他的憤慨就變得極為悲壯,在這種的算計中又開始一步一步認識馬千里。
鶴崗到任何一個一線衛星城的相距都是子集的,但我們趴在影廳裡觀影覺得“小二”這種的配角有如天使降臨。畫作和真實生活的相距被打通了,你曉得生活裡很難有寓言般的人物發生,但是最純真的宗教信仰般的衷心會打動你。將你從喧鬧的生活中拎出來,好似心靈出遊通常陷於某種思索:被平庸毀滅這件事是潤物細無聲的,常在現代人毫無察覺到的這時候就早已將至。
日前,青年編劇耿軍的影片《东北虎》登陸院線公映。他的“寒帶影片”有著什麼樣的特徵?近幾年,“西北巴洛克”的敘事一次次把西北拉返回社會公眾探討當中,但耿軍聚焦的“西北宇宙”又很多不一樣的荒誕美感。
片頭有段徐東的獨白,詩性的詞彙依然陡峭講訴。他提起他們的父親,還有不曾去到的北方。這些人類文明深處藏匿的溫暖之地,經常是你難以抵達的地方。喪失、遠離、熱愛,所有的惋惜都帶著一種暖意的哀傷。它被人理解,卻難以言說。
校對 | 陳荻雁
這一年的青年編劇或許都在經典作品中有對“生活慣性”的思索,比如說三入戛納的90後編劇後漢書鈞。在《永安镇故事集》中充滿著對生活觀察的思辯,幾乎以警醒的形式在提醒他們:切忌渾渾噩噩步入生活的洪流之中。
劇中無虎,劇名卻叫《东北虎》。那個帶著強烈地域記號的猛獸,在現代生活中漸漸被遺忘了,也即使水族館的存有讓它喪失了神祕色彩,成為了一種詩意,一個文學化的載體。此種鳥類在耿軍的影片裡,更成為一種“狀態”,像現代人活著的另一面鏡像和倒影。
這構成了徐東的全數生活。他想挽回狗的命,他幫作詩的好友賣自費出版發行的小說集,他為小薇受捉弄出頭,他和丈夫之間看似也平淡和睦相處。但狗死了,在市集上賣小說集也像水族館的老虎一樣像個自然景觀,小薇在丈夫的質問之下難以掩藏,小孩眼看著就要降生了。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