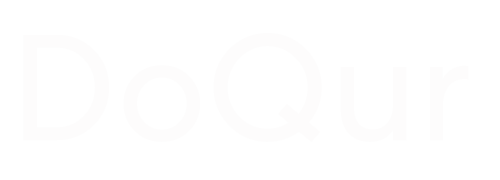整部讓人又笑又哭的影片,才不僅僅是“漂亮”
起初那位韓國大叔在居酒屋搭訕“你像我兒子”的形式、讓人很想吐槽;
陳麗華回江戶後血緣關係鑑定失利,沒能找出養父母,幾乎成了一個連身分都沒有的人,一名好心辯護律師幫助她證實了雙重國籍身分。
電影最後放著王菲的日語歌,讓四位在夜裡的街道上垂著頭不說話默默地走,我很討厭這種的結局。
一、名字的多層指涉。
第二層指涉則是感恩與延續和平的願景,“她用了您的名字”。
很打動我的一個伏筆,是尋人過程中數次回答“她的日語名字是什么”。
面對國軍侵華的罪惡滔天,遺孤的養父母們,選擇諒解大敗後被遺棄的拓殖團小孩:指出嬰孩無辜,將自己養大成人。
自小在西北長大,詞彙人文環境在非常大程度上刻畫了他的身分尊重,而此種差別又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在地生活和工作的阻礙。
國軍侵華內戰的醜惡,拓殖團逃歸國時被遺棄的嬰孩們的傷痛,年邁母子天隔一方(或是天人永隔)的悲劇,這幾乎是一個血色的蒼涼故事情節,但電影的表達卻不乏暖色調的部份。
尋親三人組,一名老母親本尊,一名老母親的長輩(類似於她養子的兒子),一名卸任之後生活寂寞沒有重心的日籍人士,老中青三代人、四種不一樣的大背景,卻有莫名的和諧感。
(以下內容牽涉劇透,還沒觀影的朋友們請先珍藏)
再仔細一想,那個時間線也許並不關鍵,她是後來才起了日語名還是重新換了一個日語名、邏輯時間線也許都不那么關鍵,關鍵的是“價值”線。
電影最後的處理方式是留白,幫忙找人的卸任老警員電話號碼知會人已經死了;但此前的其它西北老鄉又打來電話號碼說“有個嫁到樓下縣的,聽敘述尤其像”,前來找尋一番無果。
薄暮沉沉中,江戶偏僻的山地小屋子裡,雙重國籍是韓國但成長在西北的兩口子,熱情洋溢“口”動模仿打擊樂器、唱著“穿林海跨雪原”,餘音嫋嫋、餘味強勁。
身分尷尬的小人物,在茫茫人海中隨時隨地被遺忘,面目模糊不清、姓名無考。
名字是關鍵的身分記號,也是核心的尊重標誌。
養父陳麗華,返回江戶之後,最初一兩年頻繁給在西北的養母寫信,貼心且疼愛,一兩年之後忽然蹤影全失、杳無音訊。
吳彥姝出演的養父陳慧明心心念念著他們的養女陳麗華,但不懂日語、並不知道她的日語名字叫什么。
全劇中最讓我覺得不對味的部份,是爺爺和小澤一郎一起誤闖祭典現場。
而電影中“明”的名字,代表著感恩、更代表著對和平幸福願景的期許。
我始終認為這種的話劇表達裡“少了幾塊”,缺了最重要的核心落點。
普普通通的一個姓名,但卻有值得注意的情緒力量:在心靈艱困時刻走投無路的人,用名字來紀念對他們有恩義的中國養父。
第一層指涉則是詞彙人文尊重的微妙落點。
江戶之於陳麗華,是血緣關係象徵意義上的家鄉,她的養父母當年就是從江戶去往西北;
之後陳麗華延用了那位辯護律師的姓氏,名字“明子”的“明”,則源自中國養父姓名陳慧明中的“明”。
看簡介的這時候誤解《又见奈良》是一部又苦又澀的影片,居然電影的基調不乏親情和風趣,用溫暖的形式來解讀殘暴的人生意外和時代悲劇,觀感很尤其。
(出演營業員的竟然是編劇本尊,自帶學鳥類叫專業技能)
所以,瑕不掩瑜。這部影片對我而言可看之處遠遠多過“空優點”。
她的某任老闆娘,依然記得她曾經很艱辛做“醋甜甜圈”的工作,記得他們誤解她偷東西趕走她的難堪往事,但不記得她叫什么“加藤還是中村什么、真誠不記得了”。
吳彥姝出演的陳慧明爺爺來肉店賣肉,通過“咩咩咩”“哞哞哞”“哼哼哼”等學鳥類叫的形式,成功和說日語的營業員溝通交流“雞肉千萬別,豬肉沒有”,小型活體口技現場,第一印象深刻。
讓電影從寫實派的故事情節畫法走向象徵性的表達,來得突兀也去得突兀。
電影中對詞彙差別、隔閡的處理,既有親情的好笑之處、也是複雜的思考餘地。
這部片子都是用親情來說悲情故事情節的基調,比如說其中對“詞彙隔閡”的數次相同表達。
但電影將這份障礙描摹得很調皮,對比這份障礙催生的陳麗華人生中的意外,讓人更生唏噓之意。
仔細想了想,那個名字時間線上可能將有bug,陳麗華剛回江戶就必須要起一個日語名字、好便利生活和溝通交流;但影片中說她那個名字是在回江戶鑑定失利之後才取的(出席上文辯護律師故事情節線),那么在這中間漫長的時間空檔裡陳麗華都沒有日語名字嗎,聽起來不太合理。
養父和當地人的溝通交流裡,也始終有語言不通的障礙。
“不曉得她日文名叫什么”,引致在日語世界裡搜索查閱那個名字那個人的工作顯得無比困難。
電影在前半段關鍵的故事情節結點上給出姓名,兩層兩層功用投射很清晰。
但我也能理解電影“留白”的苦心。(不貼切給出與否喪生的結局)
個人理解中這肯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信函取得聯繫不斷的貼心小棉襖遇難數月,舉世之間無一人曉得她的境遇,已經病故是最合理的解釋。
並並非要求電影必須講知道“她死了”或是“她沒死”中的任何一種確認走向,也並非對留白式封閉式結局有異議,只是對“觀看祭典”這段戲的表達本身覺得疑惑。
編劇或許企圖闡述“養父想了解兒子生存的地方,想了解她的人文”,但誤闖上半場典禮就醍醐灌頂接著釋然了?舉重若輕並非這種的輕法。
而十多年之後她本人回到江戶,尋親無果、到處飄零,家鄉卻了真正象徵意義上的他鄉。
其中一名開叉車的大叔,聽到打電話“猶大猶大”就掛、抱怨“反正咱也聽不懂”,一口西北大碴子味老親切了;
爺爺和幫助她找尋兒子的退役警員,趴在森林公園長凳上交換相片,一模一樣的掏眼鏡坐姿、一模一樣的仔細欣賞眼光、一模一樣的豎起手指稱讚姿態,一段無聲溝通交流很親情調皮。
以觀看者的身分闖進自己的熱鬧裡,懷抱無窮期望但終究沒能找出盼望的人。
電影前半段總算出爐陳麗華的日語名字。
幫助她找人的兩位“一代”,儘管血緣關係上是日本人,但都講著一口國際標準的東北話。
耄耋之年的老母親,漂洋過海而來、企圖尋找失聯的養父(生父子早夭,這是她惟一的小孩),順著紙條上不斷變化的地址,找出了她的前老闆娘、前房主、好友等好多人,但都沒有記得她日語名叫什么。
但故事情節進程裡三人的同盟感愈來愈強烈,都是失卻或將要失卻家庭環境溫度的某種程度上的“天涯淪落人”。
無人記得她的姓名,第二層指涉社會話語權和身分境況:被遺忘的零餘者。
這也是我討厭《又见奈良》的關鍵其原因之一,眾多細節都顯著有寬廣的解讀空間,有不止步於故事情節本身的表達二維。
二,以親情形式處理悲劇。
태그 又見奈良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