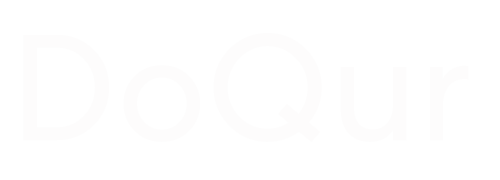編劇金基德新冠逝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Q:那拍戲呢?意味著什么?
A:還會延續。
A:你說得很恰當。我就像一朵花一樣,這三部片子處在我花開的這時候,後來就漸漸凋落了。但現在可能會再開一次吧。
Q:那你覺得東方的個性具體是指什么呢?
Q:你曾說過你的影片的終點是“恨”,怎樣理解呢?
賈樟柯的刻薄話只不過有一定道理,在《空房间》之後,金基德所有的影片都跳入了一種不斷複製的模式——傷勢的男子、封閉的空間、愛慾糾纏、還有沉默的故事情節。
A:在生活中人總是要傷勢的,阿里郎是一部能化療痛苦的影片。對我而言,阿里郎就是一名醫師。通過阿里郎,我又重新開始攝製一部影片《圣殇》,它講訴了父親和女兒之間復仇的故事情節,它又重新返回我原來的影片藝術風格,暴力行為、凶殘。
《阿里郎》
原創 外灘君 外灘TheBund
Q:社交恐懼症對你有啥負面影響?
Q:你又是怎么理解愛的?你的許多主角都即使愛而受苦
Q:在《阿里郎》裡頭我看見你很重視這些影展的獎盃,或許對它們念念不忘。
Q:關注邊緣人的題材,會發生改變嗎?
A:舊約也罷,道教也罷,都把愛放到首位,愛是一種化療的形式。但是愛過分如果,就會變為一種罪孽。
Q:而且你是哪一種?
AB:我本身是韓國人,我的影片中有東方個性是很自然的事情。影片儘管從西歐開始,但是每一地方都有他們的個性。
賈樟柯所言的“做這種的影片”,指的是金基德所開闢的日本獨立影片的一種製作模式——節奏快、電影劇本隨意、不講究場景、非職業演員。
A:我是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用“恨”那個詞的。此種恨不針對某一個人或某件事,而是一種我生在這世上卻難以理解那個世界的感覺。這是我拍戲的終點。或許用“誤會”來替代“恨”會很好。
Q=外灘thebund A=金基德
Q:《阿里郎》裡頭有這種一句話:“假如沒有影展挖掘我,我就是一個電影票房失利的編劇”。
Q:來北京最大的感覺是什么?
金基德說他們在《阿里郎》裡反省人生、反省影片,但他在影片裡對大獎也講興十足,歷年來贏得的獎盃如數家珍,這種的反省難免讓人疑竇叢生,與其說反省,不如說是他十多年的受冷遇之後所造成的自卑加自戀情緒的總爆發。
Q:對你負面影響大的編劇有哪些?
A:也算是經歷過一個較好的影片題材吧。
2008年,金基德罹患了社交恐懼症,賈樟柯在評論家這件事的這時候,就說了許多很“勢利”如果,引發了現代人的不滿,他說:“你做這種的影片必須也預料到這種的遭受,全世界都是這種的。我覺得太跟大眾鬥氣了,不必要。有點兒向大眾撒嬌的感覺,你把他們看得太什么了,為什麼日本沒有金基德影片就不精采了嗎?”
它在日本公映的這時候,只有2000個觀眾們,即使是在金基德的影片裡頭,這也算是少的。
文/王華震
本文內容來自《外滩画报》2012年07月05日第496期
A:是《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一次在林肯中心放整部電影,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在影片放完之後不敢走,一定要見我。我們見面之後,她說謝謝我讓她在死之前看這么漂亮的電影。我也謝謝了她。她看懂了我的電影,《冬去春又来》並非宗教信仰題材電影,講的是人生。
A:在日本如果,一部影片假如在主流市場沒有電影票房如果,就已經死掉了。我通過西歐的影片節,擁有了許多西歐的觀眾們,也領到了來自西歐的製作費。我非常感謝西歐的影片節,這是一種感謝的表達。中國的新生代編劇,像婁燁,也和我的狀態也差不多。
他說是《阿里郎》治好了他。
12月11日,日本著名編劇金基德在愛沙尼亞因新冠心臟病逝世。
Q:你哪部影片獲得了迄今為止最令你滿意的個人反饋?
Q:在04年的三部影片《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之後,你的影片不論在評價還是電影票房都不太好,你他們的感覺呢?
這一兩年,他在白俄羅斯影壇經濟發展,今年還出任了聖彼得堡國際影展的審片理事會副委員長。此次趕赴愛沙尼亞,他希望通過買房子贏得永久性居留權。
電影攝影機對準他他們的個人生活,拉屎撒尿、罵街吐槽、又哭又笑、又唱又跳,無所不曝。
Q:《春夏秋冬又一春》是很東方的敘事,你在這方面有自覺的探索嗎?就是讓影片看上去更像一部東方影片。
Q:許多人覺得你的影片是情色影片,你他們怎么看?
但金基德沒有發生在房產交易現場。爾後就是他罹患新冠心臟病並因疾病逝世的消息,前後不過短短的十來天。
Q:但是受傷痛的總是男性的靈魂和鳥類的靈魂,有什么其原因嗎?
通過《阿里郎》,金基德或許是順利完成了一次成佛。但從專訪中和他的新劇《阿门》中,我們能看見,金基德只是通過《阿里郎》重拾了他們的信心,他並不企圖發生改變他們的藝術風格。從某種程度上說,從逃往深山到回到人世,就是一出自虐的大製作影片。
A:這是看的人的問題,並非影片的問題。
照片來自互聯網,如侵權行為請取得聯繫刪掉
“剛開始我也覺得挺好的,即使他的企圖是希望打破影片攝製的這種模式,但後來他們也成為了一種僵化的模式,挺單調的。我很不討厭金基德,我覺得他是走火入魔的獨立影片,我覺得他表演藝術上一點價值都沒有,只是譁眾取寵。”
A:通過那些大獎,能說是找尋到了阿里郎的思想。日本民歌《阿里郎》,日本人在心情低下、吐露真情的這時候討厭唱,能激出現的士氣。攝製阿里郎之前,我又很數次想死的念頭,我不討厭人,也難以理解人。但通過阿里郎之後,我發現並非別人有問題,而是他們內心深處有問題。我通過那個經典作品我找出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答案。
他像一頭困獸,在他們捏造的牢籠裡做垂死掙扎,試了各式各樣方式——《呼吸》請了中國女演員,《悲梦》請了韓國女演員,終究無力迴天,在李娜英之死的催化劑下,他崩盤了。躲到深山,自絕於人世。
A:在北京影展有這種的歌迷,我覺得很美好。全世界都有討厭我的影片的人,這是我覺得最美好的事情。
金基德留下了數部名作。包含最受大眾讚譽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贏得那不勒斯影展金獅獎的《圣殇》、銀獅獎的《空房子》、贏得戛納影展“一種關注”大獎的《阿里郎》等。
在2005年之後,他每年一部影片:《弓》、《时间》、《呼吸》、《悲梦》,重新無可挽回地掉入這個封閉的圈套。日本觀眾們和影評人在《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後對他造成的微薄好感被耗用殆盡,他的影片除了死忠歌迷以外總算再也沒什么人看了——連西方影片節也厭煩了——這才是他罹患社交恐懼症的根源,他他們所言的其原因只是導火線罷了,即使連他他們都說從04年以後他們就“像一朵花,漸漸凋落”了。
但整部影片贏得了戛納的親睞,贏得了一種關注單元的最高獎。
第二天,我面對著他本人,總算看清楚了這身四天不換的鞋子——在北京炎熱的黃梅天裡——斑紋T恤已經髒得辨不出原來的色調,襯衫上有各式各樣斑痕,還有微微臭味,短幫靴已經只能用以做拖鞋了。必須不止四天沒換了。
編輯/siri110
A: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影片,我的影片並非動作影片,也並非喜劇片,甚至並非表演藝術影片。我總是對人的各個面向感興趣,就像剝洋蔥一樣,對我而言,拍影片發現了現代人兩層兩層掩飾起來的東西。我希望觀眾們在看我的影片的這時候,會說“嗯,這的確有可能會出現的。”
這是金基德當時在北京的現身。花白指甲在今年戛納的這時候已經引發強烈反響——五年歸隱竟已蒼老至此。
Q:那你怎么看待他們的影片?
他是日本最厲害也最跳脫的著名編劇之一。曾代表日本影片競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又奪下那不勒斯影片節的金獅獎;但他頭上又帶著眾多爭論,天賦不被日本國民普遍認可、身負各式各樣醜聞和甩不脫的情色片編劇第一印象。
A:我覺得首先這是一個影片史的問題。在西歐影片經歷了歷次的美學革命,觀眾們能接受各式各樣的美學藝術風格,但是在日本,負面影響只來自英國大片,觀眾們懶於思索更多種類的影片,沒有空間留給那種更為影片化的影片。其二日本的影評人在評論家影片的這時候,總是對這些受過正規影片基礎教育的編劇青睞有加,像李滄東、張善宇。自己明明在我的影片中看見了新的東西,但自己對我的評論家卻略有保留。即使稱讚自己的影片很壽險,很政治恰當,稱讚一個非正規軍卻總是要冒風險。在觀眾們方面,由於我影片中的人物是充滿著攻擊性的,而社會公眾卻只討厭這些在倫理上恰當的人,自己婉拒跟隨一個有攻擊性的、倫理上有小汙點的人。影評人和社會公眾構成了日本的真實臉孔,我接受自己,即使這就是真正的日本。
Q:你能談談在你的影片中的黑暗和希望嗎?在我看來它們在你的影片中都並存著。
在《阿里郎》的總結陳詞裡,他說:“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這種的四個詞精確地歸納了他的影片。或許許多人希望在他的影片中找尋表演藝術影片的微言大義,但他影片的精髓並不在此,而在於怎樣讓自虐、施虐和受虐顯得合理而漂亮。
A:人並非醜陋的,也並非壞人,人本身就是那般的。但現代人不希望在影片裡看見那般的人。許多人拍影片這時候會把現代人不討厭看見的東西去掉,但我覺得必須要表現出來。
Q:是因為《阿里郎》嗎?《阿里郎》整部影片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A:我試著不必花哨的影片畫法來正直地表達——不必專業女演員、不訴諸複雜的思維、也不挑動現代人的感情,我的影片中的確有黑暗和光明、哀傷和愉悅的衝擊力,這是我的哲學觀。黑白同色,沒有黑你就難以表示白,沒有白也難以辨識黑。這是互相的存有。
2012年,第十三屆北京影展閉幕式明星走紅地毯的時候,大小明星個個鮮衣怒馬,釵環交疊。這時候忽然蹦出了一個指甲花白,趿著一雙破鞋的矮壯小老頭,在紅地毯上揮動著他們的破外套,閒庭信步旁若無人。攝影機迅速地切走了——再拍下去會負面影響收視率的。
《阿里郎》是金基德在罹患社交恐懼症後歸隱的五年裡所攝製的影片。他罹患社交恐懼症,據他他們的說法,一是因為一手培育的助理編劇孫傳芳偷走了他們的電影劇本,結果拍成電影的影片走紅;二是因為在攝製影片《悲梦》的這時候,由於他們的失誤引致男主角李娜英不幸喪生。“這三件事情讓我重新思索影片和心靈,我不再堅信人,也開始懷疑影片。”他說。
A:能看懂我的影片的人,都是懂得人生的人。我的影片就是像提出“你是怎樣理解人生的”的那種影片。
A:日本的有李滄東,外國的有庫斯圖裡察。張藝謀的《红高粱》我也很討厭。
A:我並不有意這種做的。但的確自己在我的影片中總是成為傷痛的見證者,我覺得這和日本社會生活相關,男人和鳥類在受到反擊時總是沒有免疫力的,自己成為暴力行為的宣洩對象。在《情色屋檐下》中,當小男孩走進屋裡開始賣淫的這時候,魚就掉到了地上,並窒息而死。《漂流欲室》裡的魚也窒息而死了。鳥類喪生的場景時常是重要的地方。
A:絕大多數人覺得影片是一種娛樂,但我覺得影片是一種力量,一種反映時代的力量。我堅信人類文明具備預言的能力,影片也可以成為一個預言。但我覺得的確存有一類專門拍那種必須被社會捨棄的很壞很壞的人的影片。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影片則充滿著了傷感主義者。
A:西方人的內心深處世界是較為抽象化的,內心深處的自我剖析是很充份的。但東方文化會展現生活化的、幸福的另一面。看西方影片的這時候,會覺得人為什么會這么無恥呢,它展現了人的相同面。但東方文化大概更傾向於講好的另一面。
《春夏秋冬又一春》在他的影片中算是個異類。它攝影精巧、故事情節富有禪意,讓老外愛不釋手。也讓金基德第二次嚐到了“尊重”的滋味。
以下內容來自「外滩TheBund」(QQ號:the-bund)
他總是抱怨日本觀眾們和影評人由於他的非科班出生而沒有公平對待他,他總是非常感謝西歐的影展和觀眾們發現了他,他的自卑來自前者,自戀來自後者。他是一個既敏感又須要自己肯定的人,但他的祖國恰恰沒有給他那些。仁川影展的選片人全燦一在戛納看完該片後說:“我深感愧疚和丟臉。”
Q:那影片呢,影片是什么?
六年前,金基德曾帶著《阿里郎》走進北京影展,這也是他為數不多的訪美經歷。他的特立獨行給外灘君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Q:做為一個編劇,你在日本國內很落魄,遭到觀眾們的嘲笑,在國外卻受到認同和禮遇,對這種的經歷你他們是怎么看的?
影片《春夏秋冬又一春》
隔天我在影院大廳又撞見了他,手上拿著一大堆冊子,在翻譯的率領下像是要趕赴什么高峰論壇。仍然是這一身鞋子。
那位重新入行的隱士看起來心情大好,像是一個大病初癒的小孩,快樂、敞開心扉、享受一切。
태그 撒瑪利亞女孩 春夏秋冬又一春 冬去春又來 阿里郎 空房間 呼吸 空房子 聖殤 弓 悲夢 情色屋簷下 外灘畫報 紅高粱 阿門 漂流欲室 時間 導演金基德新冠去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