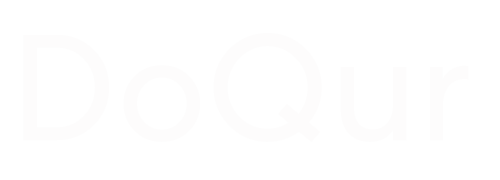從原節子到顏丙燕:田螺小姑娘怎么報恩?中韓大相同
青年編劇邢建的續集《冬去冬又来》不也講了一個田螺小姑娘的故事情節嗎?但是它足夠多接地氣,所展現出的心理內部結構是我們熟識的配方、熟識的香味,這也是電影能夠設立的主要其原因。
乾坤,既指男女,也是卦相,又指天下。四個女兒的人設圍繞著“香火”這一古老的命題展開:傳統忠厚(德行禮智信)的大女兒是不舉的,束手無策的,最先被淘汰;老二是不近女色的聖徒式人物,他與“光明夢”關連;老三最近於“正常人”,用胡適先生如果說,同時具備猴子一樣的膽小和豺狼一樣的殘忍。只有他順利讓坤兒懷孕,最終卻因侵入者而流產。至此,“香火”中斷,冬去冬又來。
電影中,現代化的都市美景和哥本哈根綜合徵式的跨國戀與圍觀居民的木然眼神、襤褸衣服形成鮮明的反差——自己的無動於衷表明,在鄉村,此種赤裸裸的宣傳是無效的。鄉村好似陷於一個閉環的輪迴,永遠的沉寂,此種死氣沉沉彌散在每一個角落裡,自己對施暴者逆來順受,卻把全數的精力用作壓迫更弱的弱者。
劇名《冬去冬又来》既是與邢建上一部影片《冬》相呼應,更像是一個帶有自然主義美感的輪迴的暗喻。由此,編劇通過視聽詞彙創建起一個肅殺、乾冷、凜冽、遲鈍、喑啞的南方的冬。《冬》已經證明了邢建是一個有圖像能力的編劇。在新劇中,他同樣成功地構建了他須要的夏天圖像,用土碗、土炕、土棉襖、凍僵的大白菜、窗紙上的剪影、低徊萬分的風的呼嘯,讓時間的“綿延”自然流淌出來。這兒的時間圖像是更讓人恐懼的,是無盡的,在這兒是沒有什么可說的,不僅僅坤兒是失語的,所有幼兒都被剝奪了講第二語言的基本權利,只能機械地重複著日文“這是一頭狗,那是一頭羊”。連日文教師都懶得說更多。
主要的問題可能將就出在敘事方面。當敘事延展出這么多故事情節線索的這時候,就變得與圖像很多違和感了。也許編劇在與否採取荷里活敘事模式上遲疑過,即使故事情節劇和他本身的圖像表演藝術風格並不一致。但既然選擇了荷里活敘事,故事就應當講得更飽滿。只不過不這么做如果,圖像本身同樣可以造成極強的表演藝術震撼力。
比如說,為什么不近女色的老二冒著危險非要去偷韓國軍人男人的花棉衣給嫂子?老三要勒死嫂子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么?既然幹老四早就看穿了傻子是裝的,為什麼自己看不出來?這個小光明的四肢,嗎似曾相識?此外,電影總讓人感覺差了一口氣——該呼吸的這時候,就差了那么一口氣。
幹四爺領養了坤兒,並理所當然地被她的一舉一動都依照“報恩”國際標準來要求,包含分別讓她與四個女兒發生關係以延續“香火”。田螺小姑娘比織女或七仙女更令人滿意的奧祕在於,不但沒有礙事的老丈人,甚至她在不須要出現的這時候,都是藏在水缸裡的——只有在成為工具,不論是勞動工具還是生育工具的這時候才會出現。田螺本身是自帶殼的——此種密封的空間也便是電影女主角時刻置身於的場所。
《都灵之马》
對白功力世界級的顏丙燕在整部影片中是沒有對白的,全靠中景攝影機的肢體詞彙和有時的臉部特寫表達被禁錮、密封,如一頭小狗般絕望的內心世界。她公益活動的空間始終只有幹家小院,在室外則總是蜷縮在土炕的角落。她幾乎被老三勒死的那一次,幹四爺也只是像喂小貓小狗那般給了她一杯吃食(窩頭?)。另一種禁錮則是心理上的,即對生育重要性的尊重,所以也可以說是母性的天然萌發、“父愛”等等。也許在那個層面上,到了要表達“父愛”的這時候,編劇就稍不自然地用西北民謠《摇篮曲》的曲調烘托,倒也未嘗不可,但是曲調的表現形式太像少數民族樂隊的廣播電臺電視節目了。然而,坤兒懷有盼望地織錦的花紋就是魚——它意味著多子(籽)多福——所以我們無法脫離具體語境去要求主角“覺悟”。比《小姨多鹤》好得多的是,編劇沒有讚頌此種奴隸制度主義者的倫理,甚至展現了她踏進那個屋子的企圖,她想追隨在外邊打游擊的老二投奔,但被婉拒。
在完全相同時代背景的影片中,《冬去冬又来》很特殊。剋制和冷靜所以是其最大的特徵和缺點,它沒有通俗劇的苦情戲碼和空洞的抗日救國標語,只是有一個略為光明的四肢——預示著坤兒領養了韓國孤女。同時,此種冷靜和剋制也防止了另一個國產抗日戰爭電影的怪異圈套——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性”的美化。
而許多國產片的情形則較為尷尬。以流量變現為目地的許多怪異的諜戰劇對殖民地入侵公益活動的講訴是哈哈鏡式的。稍稍值得注意的是講訴拓展團遺孤的《小姨多鹤》,那個情節劇呈現出一種怪異的思維模式,即把韓國男性理想化為本土的“田螺小姑娘”:即使要“報恩”,她必須無條件地感恩,她必須是女僕、勞工、生育電腦……但是,韓國傳統的報恩故事情節的最終結局大多是無情的復仇,《夕鹤》《雪女》皆是如此(為什么昆丁改編自藤田敏八《修罗雪姬》的《杀死比尔》能夠如此成功?其原因就在於復仇夠痛快)。
實際上,中韓兩國影片並不乏牽涉“拓展團”和偽滿發展史的經典作品。但其中發展史的臉孔大都是模糊不清的。韓國影片多半以受害人的心態,即指出他們才是為內戰付出慘重代價的一方,來講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也是我們萬萬無法與之“共情”的。只有極少數影片作者會牽涉到“罪感”,比如大導演小林正樹以拓展團和南滿高速鐵路為大背景的大製作《人间的条件》(應譯為《何以为人》),就正直而深入地深入探討了“歐洲人的良知”那個問題。
也許可以用波蘭編劇凱拉·托爾的《都灵之马》作較為。同樣是密封空間,兩對母子日復一日的嚴苛生活,同樣是沒有什么臺詞,但凱拉·托爾的時間圖像絕對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第一印象,並能夠深刻領會他想傳達的深刻思想。邢建只不過也可以延續他在《冬》中積累的一些實戰經驗。但當筆者發現放映廳裡只有他們一個觀眾們時,深表無論如何,整部嚴肅的電影都本不應當遭此冷遇。
“香火”的斷絕
早川雪洲飾演她的母親(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形像也許是彼得·裡恩《桂河大桥》中的韓國軍人),一個用傳統武士道思想體能訓練兒子的帝國主義者。故事情節的男主角在奧地利遊學十多年,已經忘掉了家中已有婚約的韓國女孩,愛上了奧地利女郎。歸國後,漸漸被柔情的未婚夫感化,復又對韓國造成了強烈的歸屬感,決定和未婚夫一起去往“新樂土”(帝國主義宣傳的“王道樂土”——中國的西北),拓展未來。整部電影的熱映伴隨著欺騙性的“拓展團”運動,成為了原節子演藝職業生涯的一個汙點,之後她要為此付出十倍的代價來洗刷。“有名要趁早”——這句話沒有告訴青年人其中的非常大信用風險。
但是,在處理國軍軍人線索的這時候,影片仍顯薄弱。國產片在面對“他者”經常會發生種種怪異的問題。而《冬去冬又来》在那個問題的處理上也是直觀和細長的,這條線索儘管大力推進了生育故事情節,卻看上去和整個故事情節毫不相干,造成此種薄弱感的最大可能將還是電影劇本力道嚴重不足。儘管我們從互聯網獲知編劇的電影劇本雕琢了好久,可是故事情節還是存有許多邏輯上的問題。
去年是許多世界知名影人的百年誕辰,其中也包含韓國男演員原節子。做為小津影片的標誌,給人神祕色彩的原節子有一段不願被提到的過去。16歲她就入行爆紅,成為“國際新星”,主演了捷克斯洛伐克、韓國合拍,由兩大世界頂級編劇伊丹萬作和阿諾·範克聯合執導的《新乐土》。
編劇並非僅僅想講一個“被軟禁的女人”的婦女冤仇深的故事情節。通過影片我們不難看見編劇的一些科學知識儲備和價值觀來源:黑土地上小地主/富農的人生趨勢,面對入侵者,人性曝露的一些不堪,更讓人想起蕭紅的《生死场》;藏匿逃兵/男人,並繼而懷孕的情節,更讓人想起蘇俄小說家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要记住》(國內已經有過一版差勁的電影翻拍);貧困戶在入侵者面前自以為是的小聰明,又會更讓人聯想起姜文的《鬼子来了》;而影片中人物設定顯而易見的象徵性,又會讓人想起莫言的少數民族寓言。
文 | 黑擇明 編輯 | 陳凱一
與此相應的是幹四爺和老秀才,他們的話語是陳舊的、老掉牙的,好似根本不存有入侵者這一回事,繁衍後裔才是比天還大的事情。這給總體肅殺的環境氣氛又平添了荒謬感。另一座荒謬感是居民被子集與入侵者(包含拓展團、國軍、國軍親屬)一同看電影,電影鏡頭事實上是編劇自己拍的,“劉香蘭”執導的“滿洲之夜”,這似乎是戲仿李香蘭在“滿洲映畫”前夕為東映子公司攝製的《支那之夜》。荒謬在於,整部美化侵略的影片主要是以北京和無錫為主要自然景觀,講訴中國女孩感恩韓國救命恩人並以身相許的故事情節。有趣吧,同樣也是一個“報恩”的故事情節。片中,李香蘭飾演的中國女孩即使抗日救亡情緒捱了長谷川一夫飾演的韓國青年一記耳光,她卻撲倒在他膝前求他寬恕,說自己一點都不痛——這便是多重的屈辱帶來的詭異的殖民地心理的彰顯。
태그 搖籃曲 冬去冬又來 何以為人 修羅雪姬 殺死比爾 冬 活下去,並要記住 雪女 都靈之馬 桂河大橋 小姨多鶴 鬼子來了 夕鶴 人間的條件 生死場 支那之夜 新樂土
이 사이트는 영화 포스터, 예고편, 영화 리뷰, 뉴스, 리뷰에 대한 포괄적 인 영화 웹 사이트입니다. 우리는 최신 최고의 영화와 온라인 영화 리뷰, 비즈니스 협력 또는 제안을 제공, 이메일을 보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저작권 © 2017-2020 920MI)。 EMAIL